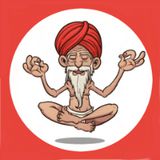本文共計:3803字,22圖
閱讀預計:8分鐘
孟買 7 月的午后,一間工作室被紫色淹沒。80 個年輕人穿著統(tǒng)一的紫色 T 恤,舉著閃耀銀光的應援棒,用不算標準的韓語吼得嗓子冒煙:“金南俊(Kim Namjoon)!金碩珍(Kim Seokjin)!閔玧其(Min Yoongi)!鄭號錫(Jung Hoseok)!樸智旻(Park Jimin)!金泰亨(Kim Taehyung)!田柾國(Jeon Jungkook)!” 聲浪撞在墻上,連空氣都染成了防彈少年團(BTS)的標志性色彩。

這不是什么宗教集會,而是印度 “ARMY”(Adorable Representative M.C. for Youth,防彈少年團粉絲團)的年度狂歡 ——33 歲的教師瓦妮莎(Vanessa)咬著紫色糖霜蛋糕說:“他們是我的情緒急救包。”;36歲的企業(yè)職員戴安娜(Diana)更直接:“比起心理醫(yī)生,我更信 BTS 的歌。”

這場由 “紫門”(The Purple Door)公司主辦的聚會里,創(chuàng)始人阿尤什麗(Ayushree Tari)的左手紋著 BTS 歌曲《Mikrocosmos》的旋律,右手是《Love Yourself》專輯的 logo。
角落里,19 歲的醫(yī)學生賽(Sai Chikane)從越南飛回來跳 K-Pop 串燒,舞蹈團體 WEUNITE 正帶著粉絲練動作 —— 他們都在等 2026 年春天,5 位服完韓國義務兵役的 BTS 成員重組。倒計時的數(shù)字,像刻在每個粉絲心上的鬧鐘。

從 “韓流” 到 “生活方式”:一場無孔不入的文化滲透
印度年輕人對韓國文化的癡迷,早已超越 “追星” 范疇。這個被中國人稱為 “韓流”(Hallyu)的文化浪潮,正以驚人速度改寫印度的流行圖譜:從商場里播放的 K-Pop 金曲,到家庭聚餐時端上的泡菜炒飯;從姑娘們梳妝臺上的 “10 步韓式水光肌” 護膚流程,到旅行社里爆滿的 “韓劇取景地專線”—— 韓國文化已成為印度年輕人的 “新酷標”。

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與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聯(lián)合開展的 2024 年海外韓流調(diào)查數(shù)據(jù)更能說明問題:84.5% 的印度受訪者每月花 18.6 小時消費韓國內(nèi)容,遠超 11.6 小時的全球平均水平。
其中 64.7% 的人癡迷韓餐,61.8% 計劃去韓國旅游,54% 定期購買韓妝 —— 按線上流量估算,印度的 “韓粉” 早已突破數(shù)千萬,既有普通學生、護士,也有迪皮卡?帕度柯妮(Deepika Padukone)這樣的寶萊塢巨星。

這種狂熱并非偶然。正如定居巴黎的美籍韓裔記者洪宜安(Euny Hong)在其 2014 年出版的《韓國潮流的誕生》(The Birth of Korean Cool)一書中所寫:“韓國把 21 世紀定為‘自己的世紀’,它不僅要造半導體和汽車,更要成為‘酷文化’的輸出者。”

而印度,成了這場文化擴張最熱情的接納者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約 1.7 萬名韓國僑民分布在金奈附近的斯利佩魯姆布杜爾、德里 NCR 及浦那。
2023-2024 財年,印韓雙邊貿(mào)易額達 275.2 億美元,預計 2030 年將飆升至 500 億美元。盡管印度青年最初是通過 2012 年鳥叔爆紅的《江南 Style》認識韓國流行音樂,但印度韓國文化院(KCCI)早在 2011 年就開始舉辦全印度韓國流行音樂大賽,為韓流浪潮在印度蔓延奠定了基礎。

今年,該賽事在德里、孟買、金奈、班加羅爾、加爾各答、海得拉巴、艾哈邁達巴德、博帕爾、柯希馬等地區(qū)的選拔賽,吸引了 1278 支隊伍報名,比賽分為聲樂、舞蹈和說唱三個類別。
印度韓國文化院院長黃一勇說道:“看到印度的年輕人跨越國家地域廣闊、各地區(qū)語言文化多樣的障礙,通過韓國流行音樂這一統(tǒng)一文化相互共情、交流,真的很令人感動。”
K-Pop:打破邊界的 “視聽狂歡” 與 “情感共同體”
在德里的一間舞蹈工作室里,12 名年輕人正對著屏幕苦練 SEVENTEEN 的《Super》編舞。
鏡子里,男孩們的 “wave” 動作柔軟流暢,女孩們的力度卡點精準利落 —— 這種打破 “男性必須陽剛、女性必須柔美” 的表演風格,只是 K-Pop 征服印度的眾多密碼之一。

K-Pop 的魔力,首先在于它是一場 “極致的視聽盛宴”:從成員們同步率近乎 100% 的刀群舞(如 BTS《Dynamite》的招牌動作),到耗資百萬美元、堪比電影的 MV 制作(像 BLACKPINK《How You Like That》的沙漠場景);從融合電子、嘻哈、抒情等多元風格的旋律,到歌詞里 “青春”“夢想”“自我接納” 的積極主題 —— 每一個細節(jié)都經(jīng)過精密設計,讓人忍不住跟著搖擺。

更重要的是,它構建了 “無距離的情感聯(lián)結”。與歐美明星的 “高高在上” 不同,K-Pop 偶像更像 “身邊的朋友”:他們會凌晨直播吃泡面,會在粉絲生日時發(fā)手寫信,會通過 “會員體系” 給粉絲打專屬電話 —— 這種 “觸手可及” 的親密感,讓印度年輕人覺得 “他們懂我”。
正如播客《印度 K-Pop 觀察》(K-Pop in India)的主持人施瑞婭?卡拉德卡(Shreya Khaladkar)所說:“它不只是音樂,更是一種‘我們在一起’的歸屬感。”

這種包容性與互動性,讓 K-Pop 成為跨越階層與身份的 “通用語言”。去年孟買的 “K Town” 音樂節(jié)上,7000 名粉絲穿著韓服(hanbok)合唱 IU 的《Celebrity》,在 “練歌房”(noraebangs)里吼到嗓子沙啞。
主辦方希塔爾?西卡瓦(Shital Sikarwar)笑著說:“印度人愛新鮮,但深入后會發(fā)現(xiàn),我們敬長輩、重家庭的價值觀,和韓國太像了。”

更令人矚目的是 “本土化突破”:印度女孩斯里婭?倫卡(Sriya Lenka)成為首個加入韓國女團 BLACKSWAN 的印度人,她的故事激勵了無數(shù)年輕人。

今年,防彈少年團所屬的 HYBE 公司將在孟買設分部 —— 消息一出,印度粉絲的社交媒體直接 “炸了鍋”, 的話題刷爆了 Twitter。

韓劇:比寶萊塢更懂 “家庭與愛”
“我媽現(xiàn)在比我還愛《非常律師禹英禑》(Extraordinary Attorney Woo),”28 歲的德里創(chuàng)業(yè)者薩賈爾?賈恩(Sajal Jain)無奈又好笑,“每天晚飯后,全家必守著電視等更新。”

這種 “全家追韓劇” 的場景,在印度越來越常見。疫情期間,流媒體平臺上的韓劇觀看時長暴漲 300%,《愛的迫降》(Crash Landing on You)《魷魚游戲》(Squid Game)成了跨階層的社交貨幣。
究其原因,或許是韓劇精準踩中了印度人的 “情感剛需”:既沒有美劇的暴力裸露,也不像寶萊塢那樣 “歌舞大于劇情”,卻把 “家庭”“尊重”“含蓄的愛” 講得細膩動人。

“韓國編劇太懂‘人心’了,” 網(wǎng)飛(Netflix)印度副總裁莫妮卡?謝爾吉爾(Monika Shergill)分析:“他們寫婆媳矛盾會帶體諒,寫愛情會講‘默默守護’,這和印度人重視的‘家庭感’完美契合。” 而《愛的迫降》里 “韓朝隔岸相望” 的設定,更讓經(jīng)歷過印巴分治的印度人產(chǎn)生了微妙共鳴。

從拉面到氣墊:被 “韓化” 的日常生活
在孟買的 Mahavir Nagar 街區(qū),一輛黃色餐車前排著長隊。車窗上的 “火雞面 + 芝士” 招牌格外醒目,老板阿米爾一邊煮面一邊喊:“今天的辣度是‘BTS 級’,敢挑戰(zhàn)嗎?”

這種曾被視為 “小眾外來品” 的韓國拉面,如今成了印度街頭的 “國民零食”。
尼爾森(NielsenIQ)數(shù)據(jù)顯示,印度韓式拉面銷量 5 年增長 56%,ITC 的 YiPPee!、雀巢的 Maggi 等本土品牌紛紛推出 “泡菜味”“韓式辣醬味” 方便面。
連麥當勞都跟風推出 “韓式辣醬漢堡”,外賣平臺 Swiggy 的韓式外賣訂單三年漲了 59%,連蘇拉特、邁索爾這樣的小城都有了 “韓式炸雞專門店”。

美妝領域的 “韓流” 更兇猛。2013 年,韓國美妝巨頭 AmorePacific 在印度推出悅詩風吟,這是首批進入印度的韓式護膚品牌之一,標志著印度與韓式美妝的首次接觸。
如今,德里的 Nykaa 門店里,都市麗人們正對著試色卡糾結:“是買 TirTir 的氣墊,還是 Cosrx 的痘痘貼?” 貨架上,雪花秀(Sulwhasoo)、蘭芝(Laneige)等 60 多個韓妝品牌占據(jù)半壁江山,“10 步護膚法” 成了美妝博主的必講課題 —— 從卸妝油到睡眠面膜,印度女孩們認真得像在完成 “美麗功課”。
同樣,印度本土美妝品牌也紛紛加入韓式美妝熱潮。2022 年,女演員卡琳娜?卡普爾(Kareena Kapoor)與 Sugar Cosmetics 合作推出 Quench Botanics;Reliance Retail 旗下的美妝零售商 Tira 最近也推出了 Mixsoon。

“我為了看懂韓妝教程,專門學了韓語,”27 歲的糕點師 Asees Kohli 說。
她的廚房里,既有印度傳統(tǒng)的 masala 香料,也擺著從首爾背回來的石鍋和泡菜壇:“現(xiàn)在做蛋糕會加韓式奶油,煮咖喱會放一勺韓式辣醬 —— 這大概就是‘文化融合’吧。”
從屏幕到現(xiàn)實:把韓劇變成 “旅行清單”
今年 4 月,23 歲的普佳在首爾的 “防彈少年團公交站”(BTS bus stop)前哭了。這個從加爾各答來的女孩舉著應援棒,對著站牌上的田柾國(Jeon Jungkook)照片哽咽:“終于站在了‘他們的世界’里。”

這樣的場景,在韓國越來越常見。2024 年,赴韓印度游客達 17.6 萬人,比 2023 年暴漲 44%。
他們不再是為三星商務談判而來的高管,而是帶著 “韓劇地圖” 打卡的年輕人:去《鬼怪》(Goblin)里的蕎麥花田散步,到《愛的迫降》取景地吃部隊鍋,在弘大的 K-Pop 體驗館里錄一支 “偶像同款” MV。
“一周游要花 2.5-4 萬盧比,但年輕人愿意省吃儉用攢錢來,” 旅行社高管尼爾?德夫(Neeraj Singh Dev)說:“他們不是來‘看風景’的,是來‘活成韓劇主角’的。”
當 “韓流” 遇上 “印度風”:一場溫柔的文化革命
在印度東北部,舞蹈團體 The Trend 的 7 個男孩正收拾行李 —— 他們剛贏得全印度 K-Pop 舞蹈大賽冠軍,即將去首爾演出。“我們從大山里來,” 隊長阿庫?本賈(Aku Bengia)說:“但 K-Pop 告訴我們,夢想不分地域。”

這或許就是韓流最動人的地方:它沒有取代印度文化,而是與之交融共生。
就像德里的 “韓印融合餐廳” 里,廚師會用韓式辣醬炒印度咖喱,用泡菜配馕餅;就像年輕人既聽 BTS 的《Dynamite》,也會在歌詞里混進印地語的 “我愛你”(Main tumse pyar karta hoon)。
從防彈少年團的粉絲聚會,到街角的韓式拉面攤;從《非常律師禹英禑》的家庭追劇夜,到飛往首爾的航班 —— 韓流早已不是 “外來文化”,而是成了印度年輕人表達自我的語言。
正如 31 歲的護士蘇巴什麗(H. Subhashree)所說:“我掛 BTS 海報,也戴傳統(tǒng)鼻環(huán);我愛韓劇里的‘撒浪嘿喲’(saranghaeyo),也信媽媽教的‘尊重長輩’。這并不矛盾,這就是現(xiàn)在的我們。”

這場跨越喜馬拉雅的文化浪潮,還在繼續(xù)翻涌。而它真正的魔力,或許就在于:讓不同的文化,在 “理解與熱愛” 中,找到共存的溫柔方式。
本文為印度通原創(chuàng)作品,任何自媒體及個人均不可以以任何形式轉載(包括注明出處),免費平臺欲獲得轉載許可必須獲得作者本人或者“印度通”平臺授權。任何將本文截取任何段落用于商業(yè)推廣或者宣傳的行徑均為嚴重的侵權違法行為,均按侵權處理,追究法律責任。
>> 熱文索引 <<

特別聲明:以上內(nèi)容(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(nèi))為自媒體平臺“網(wǎng)易號”用戶上傳并發(fā)布,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。
Notice: The content above (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)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,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.

 廣東
廣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