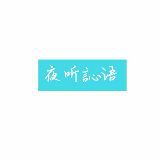“我試著銷聲匿跡,原來我真的無人問津。”
這是胡鑫宇生前在社交軟件上寫下的一句話。
遺體被發現的第4天,官方出了通報,胡鑫宇系“自縊身亡”。
3個多月里,關于胡鑫宇的消失有過各種捕風捉影的猜測,出現過很多傳言、陰謀論。
說死亡跟老師有關,說遺體發現地不是第一現場,還扯到什么熊貓血、器官買賣。
我們頭一回對一個15歲的少年展現出這么大的興趣和關心。
直到迷霧散開,才發現,少年是自己選擇離開學校,走進那片山林。
孤立無助到了極點,只想默默銷聲匿跡。
我們難以接受,一個沒有經歷霸凌、沒有和身邊人產生矛盾、沒有在家庭里受到委屈,看起來好端端的孩子,怎么就選擇了輕生?
也難以理解,一個學生,怎么會因為學習壓力大、睡不著覺這些“很正常”的問題,就想不開?
正因為我們的“不相信”,悲劇被忽視了。
胡鑫宇案落幕,但他的身后,還站著太多崩潰的孩子。
他們的內心世界,不該無人問津。


幾乎在所有人眼里,胡鑫宇都是個不需要操心的孩子。
他家境不富裕,父母在外打工,他跟著外公外婆長大,讀書很用功。
中考考得不錯,學校減免了他1500元的學費,他沒有沾沾自喜,反而遺憾沒多考幾分,不然能減更多。
成績好,努力上進,乖巧懂事,還知道為家庭分擔壓力。
符合我們對好孩子的所有定義。

但這樣一個好孩子,卻在小小的內心世界,充滿了對自己的懷疑。
他覺得自己的性格有問題:
“我這內向的性格真煩......自己就是這么一個人......”

到了高中新班級成績稍有不理想,他會內疚痛苦。
擔心老師看到他的茫然會不耐煩。
擔心自己的失眠會打擾同學的休息。
壓力大,食欲減退,注意力不集中,他會責怪自己:
“我愛發呆,思想都飄走了。”

乃至在與同學的交談以及自殺前的錄音里,多次質疑自己:
“人活著真沒意思。”
“我的存在是否已經沒意義?”
這樣巨大的反差,讓我猛然想起2年前同樣轟動的成都49中墜樓事件。
輕生的16歲男孩小林,在旁人的印象里也是上進努力。
他能把《當你老了》英文版翻譯成詩經體,在講臺上朗讀。
偶然考試失利,會主動向父母分析原因,讓父母放心。
可在QQ里,他卻經常說一些貶低自己、否定自己的話。
還曾寫下:“天天想著四十九中樓,一躍解千愁。”

還有大連那個在實驗室自殺的25歲985大學研究生。
在旁人看來,成績好,性格也開朗。
但卻會因為畢設不順,不斷責罵自己“笨”“丟人”“廢物”。

你會驚訝地發現,哪怕這些孩子已經夠優秀了,夠讓家長老師滿意了。
可他們打心底,竟根本不愛自己,幾乎厭惡自己。
這種厭惡,甚至強到要用輕生來處理自己的問題。
這些年我們看過太多青少年自殺事件,網上也有很多驚人的數據,不需要我啰嗦列舉。
但,問題是:
多少孩子,其實并非普通意義上的抑郁,而是得了“空心病”。

這個概念,是北大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老師,從多年的青少年自殺干預工作中總結出來的。
早年間,徐老師提出過一個“樹理論”。
意思是一個人就像一棵樹,樹根是原生家庭,樹干是價值觀、理想這些認知系統,樹葉是成就感、自我肯定。
人如果出現心理問題,多半就是樹根的原因。
這也是我們通常會有的想法,看到悲劇事件,第一反應就是責怪父母的教育、原生家庭的陰影。
但后來這些年,接觸越來越多有自殺傾向的孩子后,徐老師發現,不對啊。
很多孩子,根本沒有什么父母離異、早期依戀、早期寄養這些典型問題。
甚至他們和父母的關系是非常好的。
而且,人緣不錯,學習成績也優秀。
是大家眼里的好孩子、好學生。
可就是這樣美好的、閃閃發光的一個個孩子,卻覺得自己活著沒有意義。

為什么?
徐老師總結了幾個“空心病”孩子的共同經歷:
1.長期活在別人的認同里。
別人是誰?是我們這些當大人的。
老師希望ta成績好,ta就努力學習;父母希望ta聽話懂事,ta就按部就班。
ta希望讓所有人都滿意,哪怕不是自己想成為的樣子。
2.對被評價很恐懼。
比考第一更難的是什么?是每次都考第一。
尋求外部認同越久,孩子越是戰戰兢兢,因為好名次太容易失去了。
所以一次挫敗、被否定,都會讓孩子產生焦慮和恐懼。
這就是為什么能被致遠中學提前錄取的優秀學生胡鑫宇,在成績偶然出現下滑后,會心急到吃不下飯、睡不著覺、書也看不進去。
甚至多次打電話給母親說不想念了。

3.自我認同缺失。
每一個從青春期過來的人都知道,十幾二十歲是迷茫又興奮的。
我小時候就是這樣,天天思考著我到底想要什么,想成為什么樣的人,想“尋找自己”。
但長期活在大人期待中的孩子,似乎一切都是為別人而做的。
哪怕獲得了很多成功,內心還是空蕩蕩的。
這就很可怕了:找不到真正的價值感,看不見自己的意義,就很容易輕易放棄自己。

錄音筆記錄里,胡鑫宇自縊前兩次站上高樓。
“已經沒有意義了,干脆直接去死吧。”
“真站到這里反倒有點緊張了,說實話沒有理由,只是覺得沒意義。”
空心的孩子,不是想自殺,而是不知道為什么活下去。

徐老師曾對北大一年級新生做過一個統計。
他們都是剛剛從高考戰場的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贏家。
結果卻發現,其中30.4%的孩子認為學習沒有意義。
還有40.4%的孩子甚至覺得人生都沒有意義,只是照著別人的標準活下去而已。
“空心”的孩子,竟如此之眾,我們的土壤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?

環顧四周,答案昭然若揭。
我們的教育是功利的。
從小到大我們聽過多少這樣的話:
“上了高中就好了。”
“上了大學就好了。”
“畢業找到個好工作就好了。”
讀書的一切目的,在于成績,在于升學率。
就像經典的高考標語:“提高一分,干掉千人。”
就像胡鑫宇曾經初中學校的規定:每月只有一天假,以考試決定,120分滿分,考不到96分不許回家。

可分數之外,怎么成長、為人?
競爭之外,如何與世界相處?
很少有人教我們。
我們的家長是焦慮的。
曾有補習班打出口號:“您來,我們培養您的孩子;您不來,我們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。”
聽聽,多嚇人。
即便現在反雞娃、反內卷,但父母心里的“起跑線”已根深蒂固。
不信試問:雖然雙減了,可有多少家長真的敢放松,不心系學區房,不擔憂小升初?
我們的評價體系是單一的。
我們總是說“學霸”,“學渣”。
一個孩子的人品道德可以不提,但只要成績不夠好,就可以說ta“渣”。
哪怕我們的物質越來越豐富,文化越來越多元,可對孩子的評價體系卻只有成績。
可以沒有技能,但要有文憑;可以什么都不會做,只要考試考得好就行。
多荒謬啊。
但游戲規則就是如此。
社會以分數、排名、證書來衡量一個孩子的價值,父母也因為有一個成績好的孩子而覺得臉上有光。
而沒有選擇權的孩子呢?
要背上最沉的書包,參加最多的考試,最早品嘗孤獨和恐懼。
明明最脆弱的孩子,卻成了所有壓力的最終承載者,怎會不容易出問題?

一位高考狀元在嘗試自殺未遂后說:
“學習好工作好是基本的要求,如果學習不好,工作不好,我就活不下去。
不過就算好我也不開心,總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,但這樣的人生似乎沒有頭,我不知道為什么要活著。”

胡鑫宇案的調查通報里,有一個最戳我心的細節:
他將自己吊在糧庫墻外的雜林里,卻將那支記錄了生前自語的錄音筆,小心翼翼放在了風吹不到、雨淋不到的墻洞里。
或許,在生命的最后,他期待著有人能聽到他的心聲。

雖然“空心病”是時代給孩子的悲劇,可我無力怪罪任何人。
應試教育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已是最公平的路,競爭在所難免。
父母們也是第一次當父母,有要養家的操勞,還有教育壓力下的焦慮,已經夠不容易。
這是一件很無奈的事。
但,我們仍可以做些什么,讓我們的孩子遠離悲劇。
除了希望孩子考出有用的成績,也請允許ta做些“無用”的事。
娛樂,社交,愛好。
哪怕是花一上午看一片云的聚散,花一下午讀一本非“中小學生必讀”的“閑書”。
有心理學家說過:解壓最好的方式之一,就是做無功利目標之事。
別讓孩子的世界被成人的標準塞得太滿,也留一些空間,給ta自己。
除了教孩子學習的技巧,也請教給ta愛自己的能力。
告訴ta任何事情再重要,也重要不過自己的生命。
別以為自己卑微又低下,因為父親曾把你舉過頭頂;
難過時也要記得笑,因為媽媽許的愿望是希望你天天開心。
生活的勇氣和生存的信心,足以在脆弱時候成為孩子的底氣。
離開的孩子叫人痛心,但幫助更多的孩子,還來得及。
就從看見他們的傷痛、尊重他們的喜悲開始。

特別聲明:以上內容(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)為自媒體平臺“網易號”用戶上傳并發布,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。
Notice: The content above (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)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,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.

 河南
河南